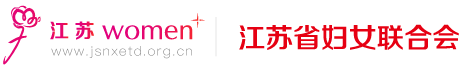雪天,等父親回家
董霞
冬日里萬物凋零,生機寥寥。而我已經習慣了在冬天期待一場大雪,這場雪宣告農民工可以返鄉,預示著歡歡喜喜的相聚,也終于迎來了我家的“家慶”。我的父親因為暈車,所以很怕出遠門,年輕時外出打工,每次出遠門都像一場歷險。父親出門時我們不知道一路是什么情形,返鄉那天總要擔心他到哪里了,有沒有走錯路,等他能平安又準時到家,才算是這一年的塵埃落定。那一天的特別之處,在一年又一年的重聚中與日俱增。父親外出打工并不固定于某個城市,武漢、蚌埠、天津等城市,他都去過。每次一去就是大半年,在臨行前他會囑咐我們姐妹在家聽媽媽的話,說他過段時間就回來了。
晚上母親給父親收拾一大包衣服,從夏天到冬天的都有,還會在最上層放上一板暈車藥。等班車的早晨,父親吃面條前就吃兩顆暈車藥,在路口等車時那板藥又捏在手里,看見車來了趕緊再吃幾顆,然后急匆匆拎上大包跨上車。我們跟著車跑,他在車里還沒坐下,趴在窗戶上招招手示意我們回家去。那時我并不覺得坐車是件痛苦的事,能從一個地方去另一個地方,多有趣。等到過年前幾天,父親回來了。
這一天就成為家里的節日,母親甚至從早上就開始準備晚飯了,地里的新鮮蔬菜、剛腌制的臘肉都燉在熱熱的小鍋子里;我們姐妹幾個負責把屋子打掃得干干凈凈,在父親到家前就擺好碗筷。一般要等到晚上,風塵仆仆的父親從大巴車上下來,全家人終于歡歡喜喜,坐在一起吃熱乎乎的飯。父親打開話匣子,就從去打工的路途說起。他要坐班車轉火車,下車了再轉班車,每次坐車都是一場歷險。有一次,他一路問人怎么走,但是在最后一趟去蚌埠的班車上,父親已經暈得分不清東南西北了,聽見播報又好像是在下一站。
車子繼續向前走了十幾分鐘,工友打電話問他怎么還沒到,一問司機才發現剛剛錯過了。司機就地把他放了下來,一個人往回走了很久才看見等他的工友。父親是笑著說的,說暈車真不好受,暈暈沉沉的,還容易緊張。晚飯后,父親臉色變得紅紅的,他一直微笑著,仿佛擺脫了暈車的不好記憶。這一年的歷險告一段落,我知道明年又會有同樣的等待,當然也會有雪后特別的,屬于我們家的團圓節日。如今,父親年紀大了,不再外出打工,每年坐車外出的人變成了我們。但暈車的痛苦成為父親揮之不去的記憶,他依舊害怕坐車。
前段時間堂姐要遠嫁,小叔招呼父親跟著婚車一起去看看,他猶豫了很久還是拒絕了。小叔有點生氣。我勸父親,又不是坐大巴車,坐私家車也不行嗎?他有點難為情,還是說,不想坐車了,暈得很。人們懂得用借口躲避難堪,是因為含蓄是每個人心中固守的修飾。只是當時不知道,沒有設身處地的經歷,輕飄飄的過往像一段簡單的故事。最后姐姐說,她陪著去堂姐家。她又說起我剛畢業去實習那天,她答應去車站接我。
可因為突發原因需要臨時換路線,姐姐問我自己一個人行不行,我在車上倒沒覺得害怕,說可以的。沒想到父親知道了,打電話給姐姐,讓她可以的話還是來接我。父親對姐姐說,以前他一個人打工時,最害怕坐車,在很大的車站里不知道哪里是出口,又不好意思一直問人,摸索著不知道跑了多少彎路才找到。父親說聽見我的聲音有點緊張,肯定也害怕找不到路,他想著想著嗓子都酸澀了,等姐姐接到我才放心。原來他害怕坐車,是一直以來的心理陰影,原來這就是他笑著對孩子們說出口的緊張。父親曾經說:“只有下雪了,能回家的那天才不害怕坐車。”
那一天對我們孩子來說,是父親打工回家了,一家人開開心心地吃大餐。其實對父親來說,這天是他期待了一年的返程,能用團圓的興奮沖淡旅途的不安和緊張。往返于鄉村和城市之間,大約占據了他青壯年的大部分時光。不管是否情愿,生活總是催促我們邁步向前,我們整裝、啟動、跋涉、停步,偶爾遇到同樣的事,偶爾期待一場大雪才能感同身受,才知道父親為了我們,在外地打拼的并不簡單的故事。
我又想起,每次外出時父親都會發信息問:“到了沒有?這次出去,大概什么時候回來?”他擔心我會像以前的他,迷失在路上,就如同我小時候擔心他一樣,現在我們互換位置,我知道他一直在家里等著我。路途漫漫,命運流轉,落在一個人身上變成不經意的后遺癥。在這場后遺癥的影響下,我們家里也有一些特別的保留,我們默契地認為一場大雪過后,是一個值得慶祝的日子,要團團圓圓地在一起吃大餐,再說說今年發生的事兒。親人相聚那天,在每個家庭里都是最值得慶祝的日子。
這份美好漸漸彌合了曾經的難堪,如今,我們不用在冬日里等著暈車的父親坐車趕回來,他閑下來就料理門前的花花草草。而我換了一種方式,說帶他去外面看看更漂亮的綠植,他沉思一會兒,說好的,那我們慢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