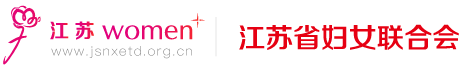天氣漸漸涼下來,醬豆子被端上了餐桌。
在同一屋檐下,人們生火做飯,用食物凝聚家庭,慰藉家人。餐桌上那一盤醬豆子,普普通通,凝結著一家人的辛勞和愛。
每年夏天,媽媽都會煮豆子做醬,好像是害怕錯過和炙熱陽光的約定。
做醬最主要的是豆子。精挑細選的蠶豆在冷水里泡一夜,最硬的褐色外層就可以輕松褪去。之后放水里煮,這時候的火候、時間必須精細把握,我們家喜歡吃稀點的大醬,就需要把豆子煮得軟爛些,再出鍋去殼。
每每剝殼時,媽媽就把小板凳擺好,我們倆默契地邊聊天邊從水里撈豆子,撕開一個小口指腹間一擠,蠶豆米就出來了。這一擠就是一下午。門外大樹葉子搖曳不停,蟬鳴不歇,等我們終于完工,石榴葉子也已經被驕陽曬蔫泛出紅褐色,媽媽把豆殼倒在石榴樹根下面,給它施施肥,希望今年能多結幾個石榴果。
剝好的蠶豆米要經歷奇妙的蛻變:發霉。這可真是一項奇妙的發現,古時候的人們知道豆腐發霉變成臭豆腐還能吃,豆子也能發霉變成醬。
但不是隨隨便便就讓豆子長霉,干燥環境下形成的霉菌才是好菌。媽媽先給豆米裹上面粉,鋪在竹編篩子上,上面再覆上端午時節曬干的艾草。
看好的晴朗天氣果然沒有失約,幾天后柴火棚上的蠶豆長了層層霉菌,掀開來已經有了淡淡的香味。
這時候老爸就登場了。老爸的做醬技術未必比媽媽高超,兩個人為此總要爭論一番,但是大家心照不宣地把體力活交到老爸身上。他燒開一鍋水,取出柜子里的陳茶葉倒進去翻滾,茶葉在攪拌下舒展開,水也從綠色漸漸變成黃色,廚房里彌漫著茶香。
沸騰的熱水有了味道,大概十分鐘后,失去汁水的茶葉被撈出來。等茶水徹底冷卻,老爸就要下醬了。將發了霉的蠶豆米平鋪在醬缸下面,隨著茶水一次次拌進去,豆子被稀釋變得黏稠發黃。最后一點茶水倒進去,老爸已經累得滿頭大汗,他總會開玩笑:“知道我沒加鹽,汗就要掉進去了。”我也哈哈大笑:“每年你都是這么說的。”
夜幕降臨,我們抽空吃完晚飯,再灑好鹽水,醬豆子在缸里終于有了雛形:豆米結在一起裹上黃色汁水,變成一粒粒泛著泡泡的疙瘩漂在醬缸里。
今年的醬豆子工作告一段落,接下來就交給時間和溫度。
屬于父母的煩瑣結束了,后面大多是我的任務,要每天不停調換醬缸位置,讓醬豆子充分沐浴陽光;下雨了及時端回家,淋了雨,豆子就酸了。
日曬烈陽,晚露夜霜。大約半個月后,不用湊近就能聞到濃郁的醬香,那是屬于蠶豆厚重的底味,以及融合了茶葉的清香,又經過緩慢發酵形成的特有味道。老爸說再多曬幾天還能做醬油呢。
醬在晾曬過程中是不能攪拌的,小時候我就犯過這樣的錯誤,拿著筷子往里挑,結果被老爸發現先訓了我半天,然后又幫我向媽媽掩飾,說是他嘗嘗有沒有味道。這當然瞞不過媽媽,她又提醒我,熱醬一攪會酸的。
有多種意外會導致醬變酸,完美的醬在幾個年頭里會出一次。品嘗它的滋味已到秋季,盛一大勺放碗里,再用煮米水加至滿碗,跟著米飯一起煮熟,今年的醬終于能吃到嘴了。
泡在焦黃的鍋巴上,醬的濃郁香味蓋過了每道菜。爸爸媽媽用筷子蘸蘸嘗一口,廚師品鑒會就開始了:看吧,我說不能多放鹽,現在味道是剛剛好;我就說要曬霉要多曬兩天,還不夠香……
我嘗不出那么多,只覺得醬怎么吃都香,配上鍋巴最香了。
成功的醬豆子會被媽媽分享給鄰里,大家都知道今年我家的醬好,也知道誰家的醬今年又酸了,分別用的什么方法。每年都是這樣,是晚間納涼時亙古不變的話題。
醬豆子和人一樣,一年又一年地奔赴夏天、等待秋天,根據溫度、濕度的變化,緩慢發酵成長,最終不只是做成了醬,更像是一種七八月的背景,小鄉村里的夏秋傳承。
一家人一起做一件事。許多時候,就是這樣的味道成為紐帶,將我們緊緊聯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