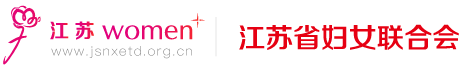先生之前加“摳”字,全因他過于節(jié)儉。
當年,先生被從省城下放,拖家?guī)Э诘降男℃?zhèn)中學,大人小孩六張嘴,生活壓力可想而知。可先生黑發(fā)梳攏,半絲不茍,身板挺直,昂首走路,加上四季中山裝,盡管有點舊,肘部還打了補丁,可漿洗得相當干凈,不像先生的老伴及孩子,衣衫沒一件囫圇的,用小鎮(zhèn)方言形容,七長八短扯皮順掉。
先生每天按部就班進中學課堂教書。他邋遢的老伴與小鎮(zhèn)的女人混得熟了,經(jīng)常提只柳條筐,下田鏟野菜、拾禾穗,帶回家里補貼日子。四個調(diào)皮的孩子更是跟小鎮(zhèn)娃娃打成一片,鉆山進溝,跳園爬樹,掏鳥窩,玩泥巴,摘果子,偷蘿卜,所過之處雞飛狗上墻,天黑都喊不見人影兒。
先生全家住在小鎮(zhèn)中學內(nèi),最初一間教師宿舍,后來得了默許,自備材料在近旁蓋了間小屋,壘灶燒飯放雜物,還擠了張不能再窄的小床。每天早晚,小屋飯香飄逸,便到先生的用餐時間了。按理先生用餐,完全可以像同行一樣上教師灶的,只為老婆孩子吃得不致太差,便放棄了應有的優(yōu)待。老伴心里有數(shù),每天為先生煮一個雞蛋增加營養(yǎng)。先生舍不得全吃完,熱雞蛋剝了皮,白白的,嫩嫩的,拿細鐵絲勒為兩半,一半含嘴里,閉起雙眼細細品嘗,另一半扣碗中留第二天享用。
先生不懂事的孩子,會偷吃那碗中的半個雞蛋,惹得先生老伴在校園里追打喊罵,饞鬼啊不孝啊,上綱上線很有高度。
先生吃雞蛋的摳門,老伴罵孩子的腔調(diào),是笑話也是傳奇,被鄉(xiāng)親們津津樂道了好多年。
教師灶偶爾也改善伙食。先生便帶個家什,連湯帶肉買一碗,端回小屋供老伴二次烹飪,全家食用。買了湯肉的先生提著家什獨自繞校園走好久,表情嚴肅,像思考重大人生問題。動筷之前,先生忍不住教訓孩子,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相當文質(zhì)彬彬。
先生的摳門,飲食方面大致如此。在小鎮(zhèn)中學的第十八個年頭的暑假,先生突然接到赴省城工作的調(diào)令。此時,先生的大兒子正跟小鎮(zhèn)一位姑娘談戀愛,如漆似膠難分難舍。先生征得姑娘父母的同意,突擊式舉辦婚禮,以上門女婿的形式,送兒子做了新郎,自己帶老伴跟另外三個孩子離開了小鎮(zhèn)。
再次現(xiàn)身鄉(xiāng)親們視野,是十多年之后。先生從省城辦了退休,滿頭的黑發(fā)已經(jīng)灰白,一絲不茍地朝后梳攏,身板也無法挺直,帶了幾分彎駝,走路還盡量頭顱高昂,像維護生命的某種堅持。先生帶離小鎮(zhèn)的三個孩子已都長大成人,有了各自的工作及家庭。他邋遢的老伴也跟先生鬧分手,不理不顧去了另一個世界。形單影只的先生下了班車,受到中學師生的熱烈歡迎。通過簡短儀式,先生將五萬元人民幣捐獻給了小鎮(zhèn)中學。
先生平生節(jié)衣縮食,積攢人民幣十萬元。那個年代,十萬元確實是天文數(shù)字。摳門的先生分文不留,將其中的一半捐了省城工作的單位,另一半捐了曾拋灑過青春汗水的小鎮(zhèn)中學。
捐款儀式結(jié)束后,先生被大兒媳接回了家,一個蓋滿了瓦房的溫馨小院。當年那個青澀多情的小鎮(zhèn)姑娘,不僅成了兩個孩子的母親,更成了鄉(xiāng)親們稱道的賢良妻子,情真意切勸老人在小鎮(zhèn)養(yǎng)老。
決計留在小鎮(zhèn)的先生,依然改不了摳門的毛病,喜歡粗茶淡飯,喜歡舊衣破裳。每天早睡早起,戴老花鏡讀幾頁書,便走出小院,或肩把農(nóng)具,去山洼幫兒子兒媳干活,或信步街頭找熟人閑聊。閑聊的過程,個別鄉(xiāng)親接過先生分享的廉價香煙,半玩笑半認真地說:“您退休金那么高,該吸更好的煙才是!”
先生坦然微笑不作回答,劃火柴將煙裊裊點燃,深深吸一口,徐徐從鼻腔冒出,一副陶醉至極的樣子。
先生的退休金確實不低,就是舍不得花。在小鎮(zhèn)住了數(shù)月,他便將銀行存折給了兒媳。兒媳自作主張,為先生買了新衣及好煙。先生看見,也不反對,卻從不碰那新衣,也不吸那好煙。
只在每年清明節(jié)之前,先生帶上足數(shù)的盤纏,赴省城為亡故的老伴掃墓,一次不曾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