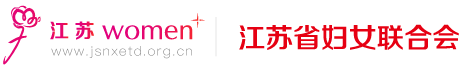1
今年七月,我到甘肅省定西市的常家河子采風,投宿的旅店名叫“山楂苑之戀”。我欣賞著店名,心中卻不以為然:電影《山楂樹之戀》的那棵山楂樹在湖北宜昌的夷陵區,不在甘肅的隴中。這般靠船下篙起名兒,可別沾上啥事兒。
常家河福興德農牧林專業合作社理事長常海增實話實說:“我們隴中,左宗棠報告皇帝,是‘苦瘠甲于天下’,從沒種過山楂,哪來的山楂戀?”
我善意引導:“您與您夫人談過戀愛吧。”
“我沒談過戀愛,我是娃娃親。”
“那是什么時候,還有娃娃親?”我默算是1970年代末。
“我13歲那年,得了頭疼病,醫院醫不好,把我放在土坑上等死。放了三天,剛分來的醫科大學畢業生聽說了,就來看我,一摸還有氣,診斷是腦膜炎,拿針在我腦袋后捅了下,我就醒了過來,再吃一些藥,命就救回來了。醫生見我窮雖窮,骨膀大,就給我說了娃娃親,是他看過病的窮女娃。”
“那您看過《山楂樹之戀》的小說吧?”我追問。常總道:“我只念到小學三年級,沒看過那名堂。人家到我們這兒來辦喜事,是咱山楂園吸引來的。”
我隨常總走進食堂外的山楂園。五彩繽紛的地毯步道穿園而過,兩旁整齊地排列著成年的山楂樹。樹高在1.5至2.5米之間,枝枝葉葉托出一簇簇山楂果,每簇五六顆、七八顆,一簇簇、一層層自然、自豪地向樹頂部壘去,滿園遍地,橫行豎列,青綠整齊,生機泱泱。
常總介紹說,春天,山楂樹開滿了白花,滿山滿眼,綠葉白花,香味兒直往鼻里鉆,蜜蜂兒直嗡嗡唱。夏季,山楂掛了果,葉子青綠,果子亮綠,山坡全部披上了綠。秋天,熟紅了的山楂掛滿樹身,掛滿田園。公司的樓前路邊,合作社的溝旁壟上,凡是空地都按每畝55株的規格栽了山楂樹,山上山下,紅紅火火。
“前年,打工回鄉種山楂的小伙子,與在村里種山楂的姑娘結婚了,就在山楂園里成的親,擺的酒。我給回鄉就業的青年們開了歡迎會,給他倆證了婚。紅花迎親驢、紅婚襖、紅蓋頭、紅雙喜大堂、篝火晚會,辦得紅紅火火。山楂樹,是他們的搖錢樹、連心樹;山楂果,是他們的愛情果、幸福果;山楂園,就成了婚戀園、喜慶園、文旅園。”常總說得滿臉都是笑容,他為家鄉驕傲啊。
2
2018年9月,通渭縣委書記找到甘肅錦華建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常海增:“常家河你老家,幾個村子八十幾戶脫不了貧,老常你能支持一下吧?”
“脫貧的標準是多少?”
“每戶年收入28500元。”
常海增算算賬,就算一百戶,總共才285萬元。好,支持。但想起聽說的一個故事,某地領導扶貧掛鉤一個村,給每戶送去兩只湖羊,期望羊長大或懷小羊,兩個月后去看長勢,羊都給殺了吃掉了。
常海增就對書記說,光輸血恐怕不行,看看有啥能造血的好項目?
書記說,出差到山東,看到那兒山楂產業搞得不錯,你們考察考察看。
次年3月,常海增請他的助手朱永峰去山東臨沂、泰安一帶考察。永峰回來后,說了種植山楂的土壤氣候要求,談了產品后期的深加工前景。常海增立即邀請山東的林業、果樹科研單位的專家來通渭縣考察,解析本地氣象規律,取樣化驗土壤和水質,結論讓他們振奮:常家河適宜種山楂。
常海增引進山楂的脫貧計劃得到了縣委、縣政府的支持。他們兵分兩路,一路去山東連根帶土買來73000多棵即將開花的山楂樹;一路在家鄉,由注資960萬成立的“通渭常家河福興德農牧林專業合作社”流轉土地1300多畝。2019年4月17日,常家河種下了第一棵山楂樹。
流轉的土地,常海增給付年租金每畝400元;出租土地的農戶招工男女各一人,來合作社種山楂,日工資100元;從春管到秋收,7個月收入4萬上下,超過脫貧的標準。經營山楂有利潤了,再給分紅每畝小麥400斤,脫貧的錢和糧有了硬保障。
2019年栽的山楂樹,2020年就掛了果,山楂紅了,山楂熟了;每樹產量50斤上下,贏得首個山楂豐收年。常家河抓住時機,舉辦了“山楂小鎮”第一屆鄉村文化旅游節,打出了“山楂小鎮”的新名片。10萬多人涌來參觀,鄉親們大受鼓舞。2021年,周圍四個村的農戶參與進來,山楂種植擴大9000畝,600多人到合作社的企業務工,五村121戶貧困戶精準脫貧。
常海增完成了縣委布置的脫貧攻堅任務,吸引并組織鄉親們走上建設山楂小鎮的振興之路。
今日的山楂小鎮,成了初具現代化規模的田園綜合體。
3
站在“山楂苑之戀”外的觀光電梯里,可以看到小鎮的西半部全景。北面,十幾層梯田鋪展而上,蓬蓬勃勃的山楂,倔強挺立的玉米,田埂坡邊青綠叢叢的各種菜蔬,用多層次的綠色著意涂染著山的土黃。西面,一幢幢白色閃亮的大棚,溫潤著各種時鮮或者稀有的果蔬。棚群外,一座大型的半山水庫,似古代書院的泮池將云天映進鏡面,幾只白天鵝在水上游弋,優哉游哉,那是常總投入500萬元修建的蓄水大塘,把山溝溝里的泥水惡水抽進來處理成灌溉水,再由27公里的黑色膠管把塘水抽送到各層梯田,滴灌那里的山楂。難怪我看到的山楂樹下都有細膠管依附著鋪設著,實施精準的滴灌,有的樹身上插著針頭,接受著營養液的滋潤。
走出觀光電梯,坡下是石刻雕像圍坐的孝悌公園,女兒給母親洗腳的塑像顯目陳列。西南處的書畫苑,是通渭縣書畫藝術之鄉的縮影;斜對面的東北處,毛澤東詩書石林公園,是大氣磅礴的精品薈萃,任誰觀瞻品味,難不心馳神往。核心區的科研綜合樓、兩幢公寓樓背后,是非遺傳統文化館。
非遺文化館與湛龍觀合署。那是一家古老的道觀,常總集資幫助修建,宮殿樓宇,雕梁畫棟,8000平方米,是山楂小鎮的一大景觀。步上三樓走廊,山楂小鎮的另一半收入眼底。
西南至南面的背陽面,峭山峻丘,溝溝壑壑,黃土中間播進了不少綠色。顯目者,是傍著山壁蜿蜒上下的鄉村公路,似一條白色的飄帶,撩開丘陵的壁壘,將山貨與希望流通起來。那是2011年農歷大年初一,常海增帶領人員、機械,推山修成的路。東南方最高的山上,設著特種動物養殖園、兒童游樂園、山楂茶館,供游人一覽眾山小。正東面,是帶著喀斯特地貌的斬龍山,幾幢百丈高的半圓懸崖柱,頂著一塊塊栽著山楂的不規則梯田,突兀凌云,令人驚嘆。中間最大的一塊梯田里,山楂樹栽成巨大的風光字:中國夢!
世代貧瘠的常家河子丘陵區,這片海拔1590多米,年平均氣溫7度上下,平均降水量400毫米左右,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為“不適宜人類生存的地方”,短短五年時間,建設成了果蔬豐產、農戶豐收、村村豐盈、人文豐厚、宜游豐樂的現代化小鎮。這是常海增振興鄉村的山楂鎮之戀!
充實并美麗著山楂小鎮的硬質道路、溫室設施、水庫光伏、噴滴管道、中藥加工、科文場館、公寓樓盤、電商服務等,福興德合作社先后投入近億元,大大超額了母公司錦華集團的注冊資金額。算算山楂年產30萬斤產值120萬,玉木耳等三大菌蔬年產收入550萬,投入大大高過產出,那成本收得回來嗎?
常海增說:“這哪能收回成本?我也沒考慮這個事。只要鄉親們有事做,有錢賺,過上好日子,我的愿望就滿足了。”
4
2021年2月25日,常海增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參加了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他披著“全國脫貧攻堅先進個人”的綬帶,聆聽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重要講話,感到無比的幸福,尤其“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斗的起點”的號召,給他以不斷奮斗的前進力量。
小時候他上不起學,父親一塊五毛錢的學雜費都借不到,沒交費就不能進教室,在外面旁聽都不行。往事刻骨銘心,那不是人的問題,而是窮的病狀。為了讓鄉親們都成為富鄉村的富農民,他要創造一個有利于農民發財、合作社發展的機制。山楂小鎮,就是他振興鄉村的創舉,念茲在茲的新機制,新農村。
因了山楂小鎮,打工青年陸續返鄉就業,外地姑娘頻頻騎驢來婚。兒童適齡上學,不再放荒;老人負暄喝茶,少見空巢。大媽歌舞于廣場,游客流連于果苑。貪污賄賂、黑黃賭毒未見蹤跡,急難愁盼、內吵外鬧鮮有發生……無怪乎來此考察的甘肅省政府領導人說常海增是“社會疑難雜癥研究所所長”。美哉,理想中的幸福苑,現實中的山楂鎮。
山楂紅了,山楂鎮美了。我對他傾情山鄉的真善美帎表欽敬。他笑道:“沒那么高大上,我連喝了一百天山楂切片茶,喝好了脂肪肝,所以我很戀著山楂呢。”
“休言漢子少文墨,萬畝山楂盡是詩”。我讀懂了這位隴中漢子“山楂苑之戀”的詩和遠方,山楂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