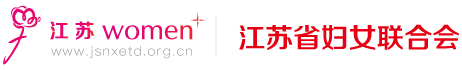“分娩鎮痛是人類之光,大力推廣分娩鎮痛技術可以讓產婦不再恐懼生孩子、從容享受做母親的快樂,在國家鼓勵生三胎的當下更有助提升女性的生育意愿。”北京大學第一醫院麻醉科主任醫師曲元近日對中國婦女報全媒體記者說,作為母親,親身體驗分娩鎮痛后會發自內心地認同和感謝這項技術。
有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平均分娩鎮痛普及率約為30%,雖然較2018年的不足10%已有了提升,但相比發達國家80%—90%的普及率還明顯偏低。為何多數中國女性還不能享受到能為她們帶來福利的分娩鎮痛技術?近日,中國婦女報全媒體記者專門采訪了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婦產科和麻醉科的多位專家,專家們呼吁,醫療機構和相關部門應不斷努力將分娩鎮痛技術在全國推廣普及,讓更多的中國女性也能享受到分娩鎮痛的人文關愛。
從吸入到椎管內給藥,100多年來分娩鎮痛技術不斷發展,成為“可行走的硬膜外鎮痛”
老話說:女人生孩子猶如過鬼門關。雖然分娩疼痛是一種自然過程,但100多年來人們一直在追求如何緩解這種難忍的疼痛。在藥物鎮痛出現之前,給產婦減痛有聽音樂、催眠、熱敷、導樂球、家屬陪伴、按摩等方法。
北京大學第一醫院麻醉科主任王東信向記者介紹,歷史上最著名的分娩鎮痛,是英國女王維多利亞生第8個孩子時,有醫生給她吸入了氯仿。當時的分娩鎮痛技術很稀罕,只有女王才可以享有。直到麻醉藥品技術和觀念飛速發展后,分娩鎮痛才作為常規醫療技術在臨床實施。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國外一些醫院會讓產婦吸入氧氣跟笑氣混合的氣體來鎮痛,但該方法鎮痛效果并不理想,且有潛在副作用。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椎管內鎮痛技術開始應用,隨著新麻醉藥物的不斷出現以及麻醉醫生的反復研究試驗,椎管內分娩鎮痛逐漸成為公認的效果最確切、副作用較小的方法。20世紀90年代后,國際上已將分娩鎮痛默認為椎管內分娩鎮痛。2000年左右,分娩鎮痛技術在國外日趨成熟并形成共識——低濃度局麻藥加上低濃度芬太尼,鎮痛效果比較好,對分娩過程中產力影響較小。“后來為了讓鎮痛效果更好,還有一些改進,比如增加了鎮痛泵,嘗試把藥物濃度再降低、增加容量,讓麻醉藥分布更平衡。”王東信說。
我國的分娩鎮痛沿用了國際上的方法和技術,如今的椎管內給藥有硬膜外腔和蛛網膜下腔兩種。“蛛網膜下腔給一點藥物就有鎮痛效果,但不能維持很長時間;硬膜外腔可隨時給藥,讓產婦一直沒有疼痛問題。”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原麻醉科主任吳新民向記者解釋,這個過程中麻醉藥物也有變化,由不能讓運動神經麻木和感覺神經麻木分開、易造成人下肢發軟的布比卡因換成了羅哌卡因,并降低了劑量。羅哌卡因可讓人感覺不疼,但運動不受其影響,被稱為可行走的硬膜外鎮痛——讓產婦有分娩感覺但沒有分娩痛苦。
“分娩鎮痛技術即使發展了挺長時間,包括椎管內分娩鎮痛我們醫院也做了20多年,但不代表這個方法就是完美無缺的。作為麻醉大夫,如何給女性提供更好、更安全的鎮痛效果,我們還在不斷研究和改進。”王東信認為,分娩鎮痛的發展和普及將是未來的趨勢,它既滿足了產婦鎮痛的需求,也體現了醫療人文關愛的發展,應該在全國各地進一步推廣普及。
麻醉醫師短缺、沒有統一收費標準、助產技術退化等,讓分娩鎮痛難以在全國推廣普及
我國地域遼闊、各地醫療水平差異明顯,因此分娩鎮痛普及率地域差異也很顯著,同一省份不同地區也有明顯差異。在近幾年“常春藤·無痛分娩基層行”公益活動中,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婦產科主任醫師尹玲發現,不少基層醫院沒能開展分娩鎮痛服務,甚至北京一些大醫院也沒有分娩鎮痛項目。尹玲認為,雖然目前要求做無痛分娩的產婦越來越多,但麻醉醫師數量短缺、沒有統一收費標準以及助產技術退化等原因,讓分娩鎮痛尚難以在全國全面推廣。
缺少麻醉醫生,是分娩鎮痛推廣難的主要原因。中國醫師協會麻醉學醫師分會2019年的統計數據表明,我國麻醉醫師數量為9.2萬人,平均每萬人配備0.6個麻醉醫師,而發達國家平均每萬人能配備2.5至3個麻醉醫師。此外,基層醫院對主導和實施分娩鎮痛的麻醉科也有誤解。“很多人認為產婦分娩期間,麻醉醫生需要一直守著無法分身做其他急診,其實不是這樣。”曲元對記者解釋,因為分娩鎮痛的麻醉藥物對產婦心率、血壓影響不大,對胎兒呼吸也沒有抑制作用,麻醉大夫給產婦打上分娩鎮痛、接好鎮痛泵,半小時后便可以離開,可由助產士繼續觀察產程。
此外,收費標準不統一、分配不合理也是分娩鎮痛難以全面推廣的重要原因。吳新民表示,“國內許多醫療機構手術室和產房通常不在一個區域,麻醉科醫生可能這邊做著急診剖宮產或其他手術,那邊需要分娩鎮痛,常常難以分身。如果再沒有合理的收費標準,大家就沒有積極性。北京是最早確定分娩鎮痛收費標準的地區,一些地方一直都沒有收費標準,或者沒有給麻醉科大夫、產科大夫和助產士合適的分配比例,所以好多醫院并不愿意做分娩鎮痛。”曲元調查發現,如今全國約有21個省市對分娩鎮痛已有比較合理的收費標準,一例價格約為2000元左右。
尹玲認為,助產技術的退化也是分娩鎮痛難以推廣的原因之一。在“常春藤·無痛分娩基層行”活動中,尹玲發現,因為沒有開展分娩鎮痛,一些地方的產婦會因為懼怕產痛選擇剖宮產,久而久之自然分娩率越來越低,有些醫院索性就取消了助產士,產婦待產只有普通產科護士幫忙準備剖宮產,這是很令人痛心的。
事實上,助產士需要參與產婦實施分娩鎮痛的全過程,一直陪在她們身邊。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產科護士長劉軍向記者解釋,分娩鎮痛前,助產士需要評估產婦情況;準備穿刺時,要提醒麻醉大夫等產婦宮縮過去、在不疼間隙盡快穿刺;在穿刺過程中,要注意產婦是否會扭動;穿刺結束后,要把產婦抬到半臥位,做胎心監護,觀察胎兒的心率、生命體征是否穩定。“助產士是分娩鎮痛中很重要一環,除了配合產科醫生和麻醉師工作之外,還要做好產婦和家屬的心理疏導,消除他們對分娩的恐懼和擔憂,如果取消了助產士,勢必會讓助產技術退化,對推廣分娩鎮痛很不利。”尹玲說。
多地已將或擬將分娩鎮痛納入醫保,全面推廣還需要標準化和規范化
如何才能在全國進一步推廣普及分娩鎮痛?早在2018年8月,國家衛健委等7部門制定了《關于加強和完善麻醉醫療服務的意見》,提出到2020年,麻醉醫師數量增加到9萬,每10萬人口麻醉醫師數提高到6.5人;到2030年,麻醉醫師數量增加到14萬,每10萬人口麻醉醫師數接近10人。2018年11月,國家衛健委下發了《關于開展分娩鎮痛試點工作的通知》;2019年3月,913家醫院成為第一批國家分娩鎮痛試點醫院。記者了解到,目前江西等省已將分娩鎮痛納入醫保,包括浙江省在內的多個地區擬將分娩鎮痛等項目納入醫保,相信有醫保政策的加持,將極大促進分娩鎮痛的推廣和普及。
此外,吳新民認為,分娩鎮痛的順利開展還必須有麻醉科、產科、助產士和新生兒科等多方面通力合作。“麻醉科大夫是藥物鎮痛的實施者;產科醫生要評價產婦是否能自然分娩,并協調麻醉大夫到產房;孕婦進產房后,助產士要進行嚴格觀察,有什么情況及時喊麻醉大夫或呼叫新生兒科來協助解決,以保證產婦和新生兒的安全。”
在曲元看來,分娩鎮痛還需借助信息化系統簡化工作流程。比如北京大學第一醫院讓麻醉醫生在產房停留半小時左右,其余時間可用電腦遠程監控鎮痛泵,在麻醉科即可實時監測產婦藥量等情況。而讓尹玲印象深刻的是,山東煙臺毓璜頂醫院把近百名麻醉醫師分為手術室內和手術室外兩部分,這樣有一定數量的麻醉醫師在手術室外專門負責分娩鎮痛和腸胃鏡等舒適化醫療服務比較理想。
劉軍則呼吁,希望國家能增加助產士的人力配比,讓更多產婦能享受到分娩鎮痛服務。“但推廣任何一項技術都需要標準化,目前條件下有的醫院麻醉藥物配方未標準化,有的醫院產科和麻醉科人力資源匱乏,尤其是助產士人員太少,很難嚴密觀察產程、減少鎮痛帶來的醫療風險。因此要理智對待、穩步推進分娩鎮痛的推廣,不能‘一刀切’。”
分娩鎮痛不僅可以減少產婦身體和精神的損傷、降低新生兒早期死亡率,還可以降低無指征剖宮產率。國家衛健委分娩鎮痛試點專家工作組組長米衛東介紹,在2017年底到2020年底的3年時間里,分娩鎮痛試點醫院的無痛分娩率由27.5%左右提高到了53.2%。
“分娩鎮痛能讓產婦體會到沒有痛苦又能分娩得子的歡樂,但分娩鎮痛深入基層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尹玲強調,“推廣分娩鎮痛不要僅限于大城市和大醫院,而要逐步推廣到邊遠地區,讓中國自然分娩的產婦都能夠享受到分娩鎮痛的福利,讓‘分娩必痛’變成快樂生育。”
來源:中國婦女報